|
| 行而有“力” 防范国际产能合作风险三步曲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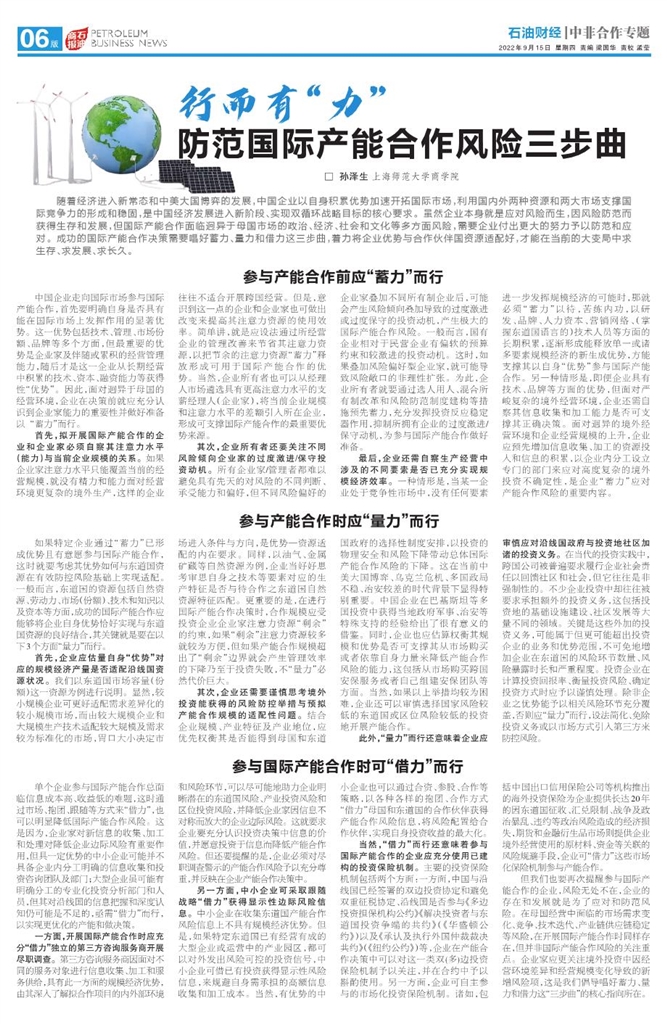 |
|
□ 孙泽生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和中美大国博弈的发展,中国企业以自身积累优势加速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大市场支撑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和稳固,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实现双循环战略目标的核心要求。虽然企业本身就是应对风险而生,因风险防范而获得生存和发展,但国际产能合作面临迥异于母国市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风险,需要企业付出更大的努力予以防范和应对。成功的国际产能合作决策需要唱好蓄力、量力和借力这三步曲,着力将企业优势与合作伙伴国资源适配好,才能在当前的大变局中求生存、求发展、求长久。
参与产能合作前应“蓄力”而行
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产能合作,首先要明确自身是否具有能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作用的显著优势。这一优势包括技术、管理、市场份额、品牌等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优势是企业家及伴随或累积的经营管理能力,随后才是这一企业从长期经营中积累的技术、资本、融资能力等获得性“优势”。因此,面对迥异于母国的经营环境,企业在决策前就应充分认识到企业家能力的重要性并做好准备以 “蓄力”而行。
首先,拟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企业和企业家必须自察其注意力水平(能力)与当前企业规模的关系。如果企业家注意力水平只能覆盖当前的经营规模,就没有精力和能力面对经营环境更复杂的境外生产,这样的企业往往不适合开展跨国经营。但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企业和企业家也可做出改变来提高其注意力资源的使用效率。简单讲,就是应设法通过所经营企业的管理改善来节省其注意力资源,以把节余的注意力资源“蓄力”释放形成可用于国际产能合作的优势。当然,企业所有者也可以从经理人市场遴选具有更高注意力水平的支薪经理人(企业家),将当前企业规模和注意力水平的差额引入所在企业,形成可支撑国际产能合作的最重要优势来源。
其次,企业所有者还要关注不同风险倾向企业家的过度激进/保守投资动机。所有企业家/管理者都难以避免具有先天的对风险的不同判断、承受能力和偏好,但不同风险偏好的企业家叠加不同所有制企业后,可能会产生风险倾向叠加导致的过度激进或过度保守的投资动机,产生极大的国际产能合作风险。一般而言,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有偏软的预算约束和较激进的投资动机。这时,如果叠加风险偏好型企业家,就可能导致风险敞口的非理性扩张。为此,企业所有者就要通过选人用人、混合所有制改革和风险防范制度建构等措施预先蓄力,充分发挥投资反应稳定器作用,抑制所拥有企业的过度激进/保守动机,为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做好准备。
最后,企业还需自察生产经营中涉及的不同要素是否已充分实现规模经济效率。一种情形是,当某一企业处于竞争性市场中,没有任何要素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的可能时,那就必须“蓄力”以待,苦练内功,以研发、品牌、人力资本、营销网络、(掌握东道国语言的)技术人员等方面的长期积累,逐渐形成能释放单一或诸多要素规模经济的新生成优势,方能支撑其以自身“优势”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另一种情形是,即便企业具有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优势,但面对严峻复杂的境外经营环境,企业还需自察其信息收集和加工能力是否可支撑其正确决策。面对迥异的境外经营环境和企业经营规模的上升,企业应预先增加信息收集、加工的资源投入和信息的积累,以企业内分工设立专门的部门来应对高度复杂的境外投资不确定性,是企业“蓄力”应对产能合作风险的重要内容。
参与产能合作时应“量力”而行
如果特定企业通过“蓄力”已形成优势且有意愿参与国际产能合作,这时就要考虑其优势如何与东道国资源在有效防控风险基础上实现适配。一般而言,东道国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市场(份额)、技术和知识以及资本等方面,成功的国际产能合作应能够将企业自身优势恰好实现与东道国资源的良好结合,其关键就是要在以下3个方面“量力”而行。
首先,企业应估量自身“优势”对应的规模经济产量是否适配沿线国资源状况。我们以东道国市场容量(份额)这一资源为例进行说明。显然,较小规模企业可更好适配需求差异化的较小规模市场,而由较大规模企业和大规模生产技术适配较大规模及需求较为标准化的市场,胃口大小决定市场进入条件与方向,是优势—资源适配的内在要求。同样,以油气、金属矿藏等自然资源为例,企业当好好思考审思自身之技术等要素对应的生产特征是否与待合作之东道国自然资源特征匹配。更重要的是,在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决策时,合作规模应受投资企业企业家注意力资源“剩余”的约束,如果“剩余”注意力资源较多就较为方便,但如果产能合作规模超出了“剩余”边界就会产生管理效率的下降乃至于投资失败,不“量力”必然代价巨大。
其次,企业还需要谨慎思考境外投资能获得的风险防控举措与预拟产能合作规模的适配性问题。结合企业规模、产业特征及产业地位,应优先权衡其是否能得到母国和东道国政府的选择性制度安排,以投资的物理安全和风险下降带动总体国际产能合作风险的下降。这在当前中美大国博弈、乌克兰危机、多国政局不稳、治安较差的时代背景下显得特别重要。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等多国投资中获得当地政府军事、治安等特殊支持的经验给出了很有意义的借鉴。同时,企业也应估算权衡其规模和优势是否可支撑其从市场购买或者依靠自身力量来降低产能合作风险的能力,这包括从市场购买跨国安保服务或者自己组建安保团队等方面。当然,如果以上举措均较为困难,企业还可以审慎选择国家风险较低的东道国或区位风险较低的投资地开展产能合作。
此外,“量力”而行还意味着企业应审慎应对沿线国政府与投资地社区加诸的投资义务。在当代的投资实践中,跨国公司被普遍要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回馈社区和社会,但它往往是非强制性的。不少企业投资中却往往被要求承担额外的投资义务,这包括投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发展等大量不同的领域。关键是这些外加的投资义务,可能属于但更可能超出投资企业的业务和优势范围,不可免地增加企业在东道国的风险环节数量、风险暴露时长和严重程度。投资企业在计算投资回报率、衡量投资风险、确定投资方式时应予以谨慎处理。除非企业之优势能予以相关风险环节充分覆盖,否则应“量力”而行,设法简化、免除投资义务或以市场方式引入第三方来防控风险。
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时可“借力”而行
单个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总面临信息成本高、收益低的难题,这时通过市场、抱团、跟随等方式来“借力”,也可以明显降低国际产能合作风险。这是因为,企业家对新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处理对降低企业边际风险有重要作用,但具一定优势的中小企业可能并不具备企业内分工明确的信息收集和投资咨询团队及部门;大型企业虽可能有明确分工的专业化投资分析部门和人员,但其对沿线国的信息把握和深度认知仍可能是不足的,亟需“借力”而行,以实现更优化的产能和做决策。
一方面,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时应充分“借力”独立的第三方咨询服务商开展尽职调查。第三方咨询服务商因面对不同的服务对象进行信息收集、加工和服务供给,具有此一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由其深入了解拟合作项目的内外部环境和风险环节,可以尽可能地助力企业明晰潜在的东道国风险、产业投资风险和区位投资风险,并降低企业家因信息不对称而放大的企业边际风险。这就要求企业要充分认识投资决策中信息的价值,并愿意投资于信息而降低产能合作风险。但还要提醒的是,企业必须对尽职调查警示的产能合作风险予以充分尊重,并反映在企业产能合作决策中。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可采取跟随战略“借力”获得显示性边际风险信息。中小企业在收集东道国产能合作风险信息上不具有规模经济优势。但是,如果特定东道国已有经营有成的大型企业或运营中的产业园区,都可以对外发出风险可控的投资信号,中小企业可借已有投资获得显示性风险信息,来规避自身需承担的高额信息收集和加工成本。当然,有优势的中小企业也可以通过合资、参股、合作等策略,以各种各样的抱团、合作方式“借力”母国和东道国的合作伙伴获得产能合作风险信息,将风险配置给合作伙伴,实现自身投资收益的最大化。
当然,“借力”而行还意味着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企业应充分使用已建构的投资保险机制。主要的投资保险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已经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沿线国是否参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的共约》(《华盛顿公约》)以及《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共约》(《纽约公约》)等,企业在产能合作决策中可以对这一类双(多)边投资保险机制予以关注,并在合约中予以斟酌使用。另一方面,企业可自主参与的市场化投资保险机制。诸如,包括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机构推出的海外投资保险为企业提供长达20年的因东道国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治暴乱、违约等政治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则提供企业境外经营使用的原材料、资金等关联的风险规避手段,企业可“借力”这些市场化保险机制参与产能合作。
但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企业,风险无处不在,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为了应对和防范风险。在母国经营中面临的市场需求变化、竞争、技术迭代、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风险,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时同样存在,但并非国际产能合作风险的关注重点。企业家应更关注境外投资中因经营环境差异和经营规模变化导致的新增风险项,这是我们倡导唱好蓄力、量力和借力这“三步曲”的核心指向所在。
|
|
|
|

